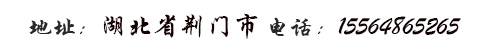兰花为何独讨文人喜爱,原来故事是这样的
|
幽兰之歌 杨炯 幽兰生矣,于彼朝阳。 含雨露之津润,吸日月之休光。 美人愁思兮,采芙蓉于南浦; 公子忘忧兮,树萱草于北堂。 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到了宋代,被视为“野草”的兰花成为“莳花艺草”,大量文人墨客开始种兰、赏兰、画兰、咏兰,兰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北宋黄庭坚是兰花粉丝后援会的会长之一,他为兰花写过一篇精美“软文”《书幽芳亭记》,可与《爱莲说》相比肩,可惜没入选“九年义务教育”,传诵指数略低。文中,黄庭坚将兰花称为“国香”,与国士、国色并列,“士之才德盖一国者,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可见推崇之深。也正是黄鲁直的这篇文章,建立起兰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 东坡居士也爱兰,他在《题杨次公春兰》中写道:“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篷艾深不见。”把兰花比作美人,形貌娟秀妩媚,自在不言之中,然幽香远溢、卓尔不群的风韵,更让人动情。真是“态浓意远,余味曲包,故得骚经之流韵。” 至明清,文人画兰之风更胜,“扬州八怪”画兰各有千秋,郑板桥更是以画幽兰、修竹、怪石闻世,他流传至今的兰花诗、画作品有近百件,为古代文人写兰花诗、画兰花数量之首。他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变之石,千秋不变之人”。郑板桥画兰出神入化,清代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曾赞道:“板桥作画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写字,秀叶疏花是姿致”。
近代,胡适写过一首小诗《希望》:“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校园歌曲”流行,这首诗被稍加修改谱曲,改名为《兰花草》广为传唱。 董必武先生对兰花的认识则非常精辟,他认为兰有“四清”:气清、色清、姿清、韵清。清则正气凛然、清白分明、清正廉洁、清雅坦荡,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 时至今日,人们用兰比喻隐士、君子,把文章美好佳妙称之为“兰章”;把义气相投、志同道合的至交称之为“兰交”;把良友称之为“兰客”,把友情契合而结拜成兄弟(姐妹)称“金兰之好”……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兰”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国学文化符号。 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必删。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huaf.com/lhfb/9271.html
- 上一篇文章: 兰花老芦头,巧做4招蹭蹭冒新芽
- 下一篇文章: 兰花,这宝贝,根深叶茂,今年翻盆一盆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