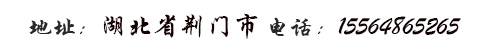江南桃花时节,唤醒关于桃的记忆
|
白癜风饮食禁忌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210210/8666093.html 故乡贫瘠的山野上,种的多是粮食:稻子、玉米、蕃薯、土豆。冬天,大雪封路、封山,人歇着,地却不歇着,雪下面,青青的麦苗和油菜顶着雪被子生长。坡地上的芦苇枯死了,灰白色的枯枝像一丛乱发,在风中一片飒飒的干响,但在根部,那些鲜嫩的新叶子却在汩汩长出来,涌泉一样,就算下雪也止不住。 父亲在黄泥山顶的菜地边,给两株毛桃施肥。肥是猪栏粪,堑在猪圈里的草混合着猪粪猪尿,起出来后堆在地角上沤,过了一两个星期,猪栏粪的臭味就不见了,换成了一种暖烘烘的夹杂着强烈氨味的特殊气体,父亲说是“肥料的气息”,他凑近肥料堆,吸吸鼻,像凑近酒缸子,似乎很享受这种味道。他掀开肥料堆最上面一层,暖烘烘的肥料味更浓郁了,肥料堆中有腾腾的白雾冒出来,像刚蒸好馒头时掀开锅盖。父亲用一把五齿钉耙,把热腾腾的肥料围着桃树铺一圈,像土黄色的脖子,围了一圈黑色围脖。 桃树吸饱了肥,枝干圆粗,呈深褐色,上面满是结疤。父亲蹲在它面前,像一个奴隶给主子请安。他摸摸它,那沟壑纵横的枝干和沟壑纵横的手相遇了,彼此都感到贴心贴肺的温暖。在余温未散的肥料包裹下,桃树一阵颤栗。父亲是个极度热爱粮食作物而对经济作物嗤之以鼻的人,家里的田地,一律不准种水果:柑桔啦、杨梅啦、李子,统统拔掉,甚至不准我母亲种西瓜和甜瓜,说是浪费地。这两株毛桃却能逃出生天,幸运地保存下来,一则因为它结的桃子确实多,二则它长的很是地方,长在地边一块斜坡上,种不了其它东西。人有时候也是这样,要么成为主导,成为话语权,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要么就边缘化,不妨碍别人。这两种人都活得滋润。我们家地里的话语权是麦子、油菜、萝卜,边缘化的是桃树,父亲手中的锄头有生杀大权,他的手也有抚慰庄稼的本事,一个老农,家乡大地上的裁缝。 二三月,桃树长叶、开花,五六月,桃子在绿蓬蓬的叶子间探头探脑。桃是毛桃,又小又瘦,硬硬的,有一个很大的核,味道却极甜,像黑黑瘦瘦又筋骨强壮的乡村少年。五月黄梅季,雨水多,多得莫名其妙,多得烦人。天空始终阴着,闷热又潮湿,每一次呼吸,都吞进去许多湿棉花般的空气,堵在嗓子眼,又吐不出,吐出来也不成,外面到处都是厚重沉闷的湿棉花。太阳虽不常见,但只要一出来,照在人身上,就针扎似的疼。动一动,浑身大汗淋漓,但空气里的水份,比人身上更多,腻腻的一层,粘在身上。梅雨天百般不好,但有一样始终是好的——桃树开始长胶了。每一次雨后,黑褐色的桃树干上,透明的、晶莹的,黄褐色或琥珀色的桃胶就会像一朵小花一样开出来。桃胶吸饱了雨水,颤微微的,果冻一样又软又可爱。采桃胶是小孩子们的活计,拎一个四方形的篾斗,低着头,在桃树底下穿来穿去。假如吸的雨水多,桃胶就会很稀,一碰就掉在地上摔得稀烂,雨水少,桃胶就成型些,但如果不经雨水,桃胶会干瘪、缩得很小,薄薄的,粘在桃枝的节疤处,采下来,混着许多脏东西,还要再泡水洗过。桃胶采下来,洗净,摊在圆匾里,晒上一两个日头,就半干了,满满的一匾缩成一小捧。成型的桃胶像一个琥珀色的QQ糖,放在手里捏一捏,软软的,弹性十足。我的家乡,管桃胶叫“桃油”,他们认为这是桃树渗出来的油汁,采桃胶,叫“挝桃油”,挝是动词,采也是动词,但采是自上而下的,很美丽,透着优雅。而挝是挖出来、采下来、抠出来的混合,野蛮粗暴,不讲章法,很符合汤溪人的特点,生机勃勃又具有野性的美。 孩子们挝桃油,是有大用处的,半干了的桃油,拿到镇上供销社去卖,三分钱一斤,一个夏季,勤快的孩子能挝五六斤,少的三四斤。我一年级上学时,学费是五毛钱,家中还不一定掏得出,有些忒穷一点的,五毛钱学费要拖到学期结束才交。父母们往往会对那些半大的孩子说,自己赚学费去!十来岁的孩子力气小,去生产队上工队长不要,田里的劳力活干不得,但还是有一些赚钱途径的,夏天挝桃油;秋天去乌桕树下捡白白的桕籽;拔猪草喂猪;割草饲牛;秋天摘茶籽;捡稻穗……我干过一个最赚钱的活是跟着外公去采草药,现在记不得是哪种草药了,印象中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开紫花,茎杆有小毛刺和硬梆梆的棱,大多长在崖下阴凉处,以及草木茂密的沟畔。挎一只竹篮,满山满畈地寻,但草药并不好找,也许一天下来只有半篮,然而日积月累,数量也可观。把草药洗干净,晒十来天,一小捆一小捆扎好,拿到供销社去。供销社的柜台像旧社会的当铺,高高的,小孩子要踮着脚尖才能看清里面的人。供销社收购站在老西门,有一个头顶圆心秃着的中年人长年坐在里面,我们把草药、乌桕籽、晒干的桃油递上去,他放在秤里秤过,拿出一把乌黑的大算盘,劈哩啪啦一阵甩,算盘的上下两排算珠便分开码得整整齐齐的。后来,我家种珠兰花、种茉莉花,也拿到收购站卖,珠兰花要在早上卖,茉莉花要在中午卖。农历六月大热的天,茉莉花浓郁的香气熏得人昏昏沉沉,走到哪里都是喝醉酒似的。 桃油虽好,量却很少,满满一大筐水嘟嘟的桃油,晒干了,只手心里一小把。而且桃树并不多,我家黄泥山顶的两株桃树是毛桃,出产的桃油要少一些,茎杆粗壮、节疤多的老黄桃,下雨过后,节疤处亮晶晶的都是。黄桃成熟的季节,正是桃油最多的时候,门前的山岗上有一片黄桃林,是外村人的,有两个老头守着,倒不是守着桃油,是怕我们偷桃吃——而我们确实经常去偷桃吃。中午,老头渴睡,吃了饭喝了点小酒,就迷迷糊糊的,正是偷桃的最佳时候。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子,潜伏在桃林边上的豆地里,看看老头不在,把衣服下摆塞进裤腰,用皮带扎紧,嗖的一声窜进去,树上的桃子,不管青的红的,一股脑儿摘下来塞进衣服,不一会儿上身就鼓鼓囊囊的,像个畸形的胖子,跑两步,或者弯腰,桃子就会从领口蹦出来。老头发现有人偷桃,大喊一声:小猢狲!站住!七八个人马上分开逃窜,老头不去追大的,专捡小的、女的追。我小时候,被这个老头追过好几次,以至长大以后还经常做噩梦,但我跑步比较快,一次都没被抓过。我拚了命地往村中跑,只要跑过那条小沟,老头就不会追了。这是无形中形成的戒律,很奇怪,没有人作过规定,但就是这样,过了小沟,就算进了自己村。老头就是再凶再狠,也只能停下脚步,悻悻地骂一句:少爷娘教的猢狲!强盗土匪出世的!父母们看我们偷了桃,也不恼,只是嘱咐一句:下次别偷了,岩后坎垅跌去怎么办! 六月底,黄桃就被摘光,卖给镇上的罐头厂做黄桃罐头,去医院看望生病的人,都会去供销社买一瓶黄桃罐头一瓶桔子罐头。黄澄澄的桃子,泡在糖水里,一年两年都不会变色,永远像新摘下来刚剖开一样。但罐头里的桃子,是腻的,甜得发腻,丢失了那份特有的清甜。丢失了桃子的桃树,空落落的,像丢失的孩子的母亲。桃叶依旧青翠碧绿,但满树累累的果实,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气,它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树下的杂草,一日一日地茂盛起来,八月草、牛不吃、羊蹄草、长毛头、黄荆、刺儿菜,仿佛几日之内就呼啦啦长出来,长到人小腿肚高。农历七八月,雨下得比较少,且大多是阵雨,刚刚还晴天丽日,呼啦啦一阵风起,暴雨劈头盖脸打下来,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太阳又如先前一般照着,刚刚过去的暴雨好似一场梦,只有衣裳是湿的,农户家晒在场院里的谷子,已被飞快地抢回家,空荡荡的院内,几只鸡在忙着争抢漏在地上的几粒谷子。这样的暴雨天气,是不能催生桃胶的,桃子没了,桃树流干了眼泪,它空洞的黑魆魆的眼眶内,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水。 这么多年,我竟不知桃胶是可以吃的,还是一种特有的美容食品,更有美其名曰“植物燕窝”,也许是父母们故意不说,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去年到丁阳岭观桃,当地农民卖炖好的桃胶,五元一小杯,买了一杯尝尝,相对美味的源东白桃,桃胶味道不过尔尔。 本期文字:张乎 图片为中国白桃之乡——源东丁阳岭的桃花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huaf.com/lhfz/11717.html
- 上一篇文章: 阴不死的珠兰花如珍珠,馥郁如兰,一棵
- 下一篇文章: 从富春花局到富春茶社一条小巷子看百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