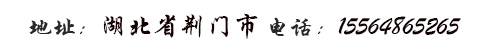漠北劲草
|
我的初中 文/陈奠华诵读:蘭花草 (原创) 一九七三年正月下旬的一天,初春濛濛的细雨下个不停,在浊港洲通往西港的泥泞小道上,一个身高不及四尺,年龄十三岁的小孩,瘦弱的身体,一件很不合体的罩衣将整个屁股遮挡着,黝黑的脸上两行未擦尽的泪痕清晰可见。干枯的小手提着一个陶瓷油罐,赤着脚艰难吃力地行走着,不时将罐子从左手换至右手,再从右手换到左手,生怕脚下打滑摔跤。渴望读书的他,深知罐里装着他唯一能上初中的学费,三斤茶油。这孩子就是我――陈奠华。 学校早已开学了,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在父母的陪送下都高兴上学去了,犹如落魄的我整天以泪洗脸,在家呆呆地坐着,人一天一天地消瘦,好象被吸血鬼吸过一样,干黑干黑的。深知儿子心事的母亲,此时,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束手无策的她只能是饮泪相伴。学校上课快过半月了,再不让儿子去学校恐是无法赶上课程了。这一天,伟大的母亲终于痛下决心,将家中唯一可以变卖的茶油,瞒着父亲私下作主给我拿去粮站卖了做学费。油只有三斤,但陶瓷油罐却有五六斤重。天刚蒙蒙亮,父亲还在睡梦中,母亲早早起床,帮我把油装好,提着油罐从后门出来,送我一程,把油罐交给我,并叮嘱我路上千万要小心,这是能让我上初中唯一的资金来源。那时上中学学费是三元四角钱,茶油粮站收购价格是1.17元一斤。三斤茶油到粮站一过秤只有2.8斤,只能卖到3.2元,还差两角钱不知妈妈从哪借来的,就这样,在开学十多天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我人生最高的学府――西港中学。 西港中学是在一所封建产物的梁家祠堂,祠堂一进三幢,两层楼,青砖与木柱结构,前幢是教室,中幢是礼堂,两边是教师办公室,后幢是学生们的寝室。学校厨房在后幢左边。煮饭工友叫周庆汗,校长李立茂,我的班主任是涂寿华老师,须然过去了四十多年,我却是记忆如新,因为我的初中太让我刻骨铭心了。 我个子不高,四十多个同学一班的我却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去得迟,班上位子早分好了,老师也只能这样安排。上课时,我基本上是站着上的,因为坐下来根本看不到黑板。正好那时学校学习也抓得不紧,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学校兴什么开门办学,课本也来得迟,我去时都还没发新书。班级上都有几分土地,每星期都有两节劳动课,由老师带着同学去种地,有时还组织去开荒。记得我们班种的是棉花,劳动课时,老师言传身教,怎样翻地,除草,下种,施肥。初中让我学到了种地的本事,却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想起来,我虽然上了初中,文化水平却比当下五年级都不及。但让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是我会种地,种地生涯伴着我慢慢从小孩变成青年,从青年到而立之年。我的初中,让我拥有几十个同学友谊,也曾学过英语,ABcD我还读得出来。只遗憾的是,当下同学聚会风行,我这个辍学的初中生不知聚会是何感觉,让人不知道我也曾经是个书生。哎!不聚也罢,勉得自尊之心又要受到伤害。 初中的那段日子还是值得追忆,涂寿华老师给我起的小名:三十斤的爱称,让我倍觉亲切。篮球场上,我无缘抢到球,同学们把球送到我的手上,只可惜我没气力投到篮中,但那份关心,那份友谊,让我难忘。还有女同学们见我无菜下咽,一个个给我碗里送来家里带的佳肴,那男女有别的年代,我无羞无畏地欣然接受,只是仗着我个子小,同学们不笑话我的资本,我享受着我家不能给我的味道。 美好的校园生活回想起来,几分感恩几分羞涩。有一次,我无米蒸饭,只有半碗薯丝干的午饭,不小心全倒在地上,眼见一餐又要挨饿的我,同学们你一口我一口凑满一碗给我,让我吃上了久违的白米净饭。肚子被同学们的浓情厚意填得饱饱的,但那辛酸苦涩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九月深秋,天暂变凉,同学们都有厚厚的绒衣秋装,我只得把冬天的棉袄带上,那另类的着装使我无法顾及脸面,因为我怕冷怕着凉。终于一天,我再无法坚持与同学们一起学习,无法一起嬉闹,没有吃,没有每星期两角钱的柴火费,我含泪离开了学校,贫困碾碎了我求学的梦想。 再见吧!我的西港中学!再见吧!我的尊敬老师!还有那同一教室,同一寝室的同学们。 这就是我的初中。 陈奠华写于.10.25日子夜 作者简介 陈奠华,男,汉族,江西修水人,生于年,初中辍学。现为工商个体户,热爱文学,闲时喜欢写作。曾在有治好白癜风的患者吗白癜风发病机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huaf.com/lhfz/21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