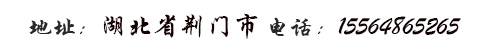高手细说兰花瓣型历史,这些瓣型的来源你知
|
常见的白癜风发病原因 http://baidianfeng.39.net/a_zzzl/131120/4294211.html 瓣型学说的诞生,在中国兰花的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里程碑意义,是中国兰花所独有的金冠。在群芳荟萃、璨若星河的花卉王国里,中国兰花因此而独树一帜,熠熠生辉、光彩夺目。自此,中国兰花的品种选育,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瓣型时代... 瓣型学说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颇多比拟。其中,尤以拟人拟物为主、以花拟花为最。兰友们耳熟能详言必及之的梅瓣、荷瓣、水仙瓣之类,即是以花拟花的典型;而蚕蛾捧、如意舌、灯芯杆等等,则是以物拟花的代表;至于鼻、舌、腮、肩等名目,显见就是以人拟花了,大致如上三类... ▲蕙花插瓶(南通博物苑兰展)... 令很多兰友困惑的是,瓣型学说中惯用此类比拟的约定俗成,客观上已导致了很多理解上的迷茫与误读,加之主观方面的各自解读所造成的莫衷一是,更使得瓣型学说如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令不少兰友们如入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既然摸不着头脑,不妨先从我们人类大脑的“运行方式”说起。姑且将我们的大脑比作一台电脑,那么当我们的大脑要存储外部获取的巨量信息时,无疑会有一个将数据进行压缩编码的过程,而当我们读取已经存入的既有信息,则是一个解码还原的过程。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编码解码与处理信息的“运算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注定天下万物留在我们大脑中的印象数据其实都是被“压缩打包”过的,这种打包体系,类似于电脑存储系统的分级树型架构,需要调用时则会被逐层级渐次打开。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对外部庞大数据信息的处理方法,所采用的是一种非常高阶的“模糊处理”法... “意象”亦由此产生... ▲蕙兰传统品种“大一品”(无锡博物苑“得天之清”兰文化大展)... 什么是“意象”?“意象”乃由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相融合而形成。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某种“意象”。“意象”往往是高度简概的,在“意象”层面,色彩、灰阶、肌理、细节等都会被忽略,所留下的只是类似于黑白线框图的某类脉络、纲领、提要,被高度“标签”化... “意象”,是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所留给我们最为原始本真的记忆。近至幼儿园小朋友的铅笔习作,遥至远古先祖留下的洞璧崖画,以及古玉、古陶等文玩,剪纸、版画等民间艺术,等等等等,无不彰显着浓烈的“意象”气息。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极具我们东方文化特色的文人水墨画,水墨技法里面,又专有一种以墨色来表现兰花的方法,即“墨兰”。古往今来的许多画家都画过“墨兰”,比较著名的如宋元时期的赵孟坚、郑思肖、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杜大绶、徐渭,近代的虚谷、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等... ▲清·马守真《兰竹图》... 这些由水墨所表达传递出的“意象”,是以中国风等东方元素所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的审美不同,国人所崇尚的是“丹青难写是精神”、“形似易得,神似却难”,似亦不似、不似亦似,似与非似之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产生诸如“梅瓣不像梅花,荷瓣不像荷花,水仙瓣不像水仙”的疑惑了。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瓣型学说修辞的缘起,自然不会是实体的形似而只会是意象的神似了... 比如说梅瓣、荷瓣、水仙瓣,基本并不是指某个瓣型的兰花整朵看起来像梅花、荷花、水仙花,而是指某个瓣型的兰花看上去具备某些其它花卉的意味,即意象神似!这种意象神似,可能是大部,也可能只是某些局部。当然,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有整体相似的,比如春兰绿云有时候的某一些开品就会像极了荷花。但这种一目了然的相似,大多数时候并不多见... ▲上:蕙兰传统品种“大一品”(太仓蕙兰展);下:电脑生成白描图...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想解码瓣型学说的奥秘,我们就要找到解锁瓣型密码的密钥。这个密钥我们姑且称之为“意象约简三步类比法”。具体步骤如下:一、将对象由三维立体转为二维平面;二、丢掉色彩,丢掉细节,只留下轮廓脉络(获得意象); 三,寻找意象之间的关联(相似度)... ▲上:红梅;下:电脑生成白描图... ▲上:荷花;下:电脑生成白描图... ▲上:水仙;下:电脑生成白描图... 聪明的兰友大概已经看出来了,第一步与第二步其实就是将实体对象约简成白描图,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几乎不必我们自己来做。比如,我们想知道梅花、荷花、水仙花在国人心中的意象,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我们传统的文人水墨、平面雕刻、版画剪纸等等是如何表现的;至于瓣型兰花,看一看那些在摄影技术诞生之前古兰谱上的双勾白描兰花图就一目了然了... ▲光绪十六年()竞芳仙馆石印本《兰蕙同心录》“集圆”双勾白描图... 如是你会发现,在意象层面,瓣型学说是如此的贴切与精妙!梅花的花瓣基本是圆的,几乎没有瓣尖(甚至有时候是内凹的);水仙花的花瓣接近于椭圆,有明显的瓣尖(这是区别于梅花瓣一个主要特征);荷花的花瓣则是略有棱角的变型卵圆(收放有度富于动感)。是故,鲍薇省《艺兰杂记》曰:“若花瓣短而头圆者为梅瓣;略尖者为水仙瓣;较水仙略长而头阔者为荷瓣;上下皆阔者为超瓣。”;朱克柔《第一香笔记》:“梅瓣如梅,团瓣不尖,荷花先论收根……水仙取钩刺者,由水仙花瓣上倒钩故也。”;方时轩《树蕙编》:“梅花瓣,瓣头如梅,又有如兜扇者;荷花瓣,瓣如荷花,其兜可勺水;水仙瓣,短阔有尖”... ▲上:蕙兰传统品种“关顶”(太仓蕙兰展);下:电脑生成白描图... 当然,此种分类是一个大的纲要。在这个纲要之下再结合国兰花型的实际细节表现来进行进一步的划分,综合起来就是瓣型学说的基本内容了。比如说,国兰外瓣的宽阔圆润是与其捧瓣的蕊柱化变异成正比的,而捧瓣雄性化变异强烈的花,不仅仅表现为外瓣宽阔圆润,又几乎没有明显的瓣尖(某些情况下表现为瓣尖内扣而造成视觉上的弱化),同时还表现为捧瓣有硬蔸、唇瓣(舌)后缩紧小(即舌硬不舒)。所以,我们会将“捧有硬蔸、舌硬不舒”与“外瓣阔圆”同时列入“梅瓣”的入选标准;而水仙瓣,除外瓣较“梅瓣”稍狭长外,有其明显的瓣尖,同时还表现为捧瓣的蔸比“梅瓣”的软、唇瓣(舌)也比“梅瓣”的大且下挂。所以,我们会将“捧有软蔸、舌大放宕”与“外瓣宽阔有尖”同时列入“水仙瓣”的入选标准;除具备捧瓣的蕊柱化变异的“梅仙”,另有一种虽不具备捧瓣蕊柱化变异,但外瓣与捧瓣及唇瓣却同样短圆宽阔的国兰类别。所以,我们将这些指征同时列入了“荷瓣”的入选标准...对于相近或“跨界”品种,于“型”下设“形”。如“水仙瓣”分“正格水仙”(如春兰汪字)、“荷形水仙”(如春兰龙字)、“梅形水仙”(如春兰西神梅);又如具备一些“荷瓣”意味却又达不到“荷瓣”标准的则称为“荷形”,需要区别的是此处的“荷形”是省略了后缀的,是“荷形行花”“荷形野大瓣子花”的缩略叫法。后缀有别,其义大变,不可与“荷形水仙”之“荷形”相混淆... ▲春兰传统品种“翠盖”... 时代的发展、地理的阻隔、语言的变迁,等等等等,往往会给我们解琐前人留下的“文化密码”带来困扰。但只要我们能正确运用“意象”这把钥匙,你就基本掌握了“瓣型学说百宝箱”的正确打开方式。无论是瓣型还是捧型、舌型、头型,乃至梗、簪、壳、肉、彩,筋、麻、砂、晕、苔,等等等等,意象始终贯穿其中... 瓣型术语中,有些比较直白,很容易理解。比如头型里的“蜈蚣钳”、“石榴头”,捧型里的“蚌壳捧”、“蒲扇捧”,舌型里的“如意舌”、“龙吞舌”,它如“凤眼”、“鸡嘴”等等;有些时候,则可能会需要一些些的背景基础和情境代入。记得多年前,曾有兰友对“蚕蛾捧”产生了疑问,因为看起来“不像”?!有的兰友则开动了脑筋,说这“蚕蛾”是不是有可能是屁股朝我们的:两个翅膀是上方两个捧瓣而屁股刚好在蕊柱位置... ▲左:蚕蛾干品;右:蚕蛾活体...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上面的问题就不会存在。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活体的蚕蛾跟“蚕蛾捧”不像,是因为受到了活体蚕蛾的双毫(触角)与双翅的干扰。而实质上,此“蚕蛾”非彼“蚕蛾”,此处所指是中药干品“雄蚕蛾”,其在制备运输存储等过程中,相对脆弱的双毫与双翅多已不存,基本只是头躯。中医认为“蚕蛾性淫,有入肾壮阳固精”等功效。旧文人多通岐黄,加之过去是一夫多妻制,文人士大夫阶层发妻之外有个三五房姨太太是寻常,另还有家姬、收房丫头等,此外,尚以“狎游”等为雅事,固多有“吃药养龟”的习俗。他们意象中的蚕蛾与“蚕蛾捧”自然是相吻合的。是我们现代人知此不知彼弄混淆了;如此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情况,在“豆壳捧”上也出现过,包括我们一些影响广泛的兰花书籍,也曾将“豆壳捧”解释为“形似蚕豆壳一端的形态”。其实古谱上写得清清楚楚,“豆壳捧”的全称是“鸡豆壳捧”。什么是“鸡豆”?学名芡实,俗称鸡豆。看下芡实花朵或果实的前端(鸡豆壳之半),你就会发现,“鸡豆壳捧”原来是如此的惟妙惟肖,大可不必在蚕豆、大豆、赤豆、扁豆的取舍上劳心费力;再比如说“桃瓣”、“柿子舌”,有兰友会基于桃与柿的实体形态与兰花不符,转而误猜“桃瓣”或是“桃花瓣”、“柿子舌”或可能是“柿子花舌”。其实,这都是因为没有掌握“意象”这个通关密钥,而走入的误区!看一下文人水墨所画的桃与柿,一切原先的疑惑都会迷雾渐散、豁然开朗。更多的事例,不再一一列举... ▲春兰传统品种“梁溪梅”... 应当注意的是,瓣型理论是一个集体创作、集体完善、取舍从众,来去自由的开放系统。历经岁月的洗礼,有些会被保留,有些则会淡出,有些会被替代。比如,蕙兰程梅、老极品的舌型,我们今天都知道是“龙吞舌”。不过兰友们可能不知道的是,“龙吞舌”其实即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新生词汇”。溯至《兰蕙同心录》,“龙吞舌”这个瓣型词汇亦未出现,《兰蕙同心录》所记述的程梅舌型,为“尖如意舌”,至《兰蕙小史》“龙吞舌”方见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尖如意舌”就逐渐被更为贴切“龙吞舌”所取代了;又如“僧鞋菊捧”。僧鞋菊是中药“附子”(亦作乌头)的俗称,因花似鹅头,别名鹅儿花。从僧鞋、鹅头的意象即可知,“僧鞋菊捧”的捧端有一个冠状凸起(比如春兰天兴、桂圆),这一类的捧型基本介于观音捧与羊角捧之间,类似于豆壳捧且极难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僧鞋菊捧”便逐渐淡出了兰友们的视野...另外,基于各自的认知差异,不同时代或时段的同一词汇,其内在含义也是有区别的,不可不辩。比如“荷”、“荷花”、“荷瓣”,我们今天所说的“荷”,基本是“荷瓣”、“荷形”一类意思,但古代不完全是。《第一香笔记》有曰:“今之所谓荷花,不过阔超瓣、大团瓣耳,人情溺于所好,故盛称之。”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基本上可以《第一香笔记》为界,在此之前,“荷”并非专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荷瓣”,其时所谓的“荷花”实质上多是水仙瓣中“荷花水仙”的简称,即后来所说的“荷形水仙”。自《树蕙编》、《兰蕙同心录》及后来的《兰蕙小史》,“荷”这个词汇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荷瓣”的专属垄断含义... 之于瓣型,于正格的“梅、荷、仙”之外,尚有别格的“飘门”,“奇、蝶花”,及“素花(色花)”等等;这些花型(花色)与寻常之花有异的的品种统称为花艺品种;而叶片与寻常之叶有异的的品种则统称为叶艺品种。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 ▲江苏春兰展(镇江北固山)... 长久以来,少部分兰友对瓣型学说存有一个莫大的误解!仿佛瓣型学说就是“梅荷仙”,乃至仅仅就只是“梅荷仙”而已!甚至有一部分兰界学者也或多或少存有这种误解,这是很要命的...必须强调的是,“梅、荷、仙、素、奇”,等等等等,只是瓣型学说广为人知的一种直观外在的粗浅呈现,是其表象而非其内核!“瓣型学说”的内核,是基于符合国人的审美与精神需求,对所有国兰品类的分类打包法,是一个国兰优新品种的遴选体系... “瓣型学说”这个词汇本身是个缩略语,是后世对这个遴选体系约定俗成的简称!全称则当是“瓣型、色、香、韵学说”。所谓瓣,是指代花,也是缩略,梅瓣、荷瓣、水仙瓣、素心瓣,全称就是梅瓣花、荷瓣花、水仙瓣花、素心花;所谓型,蕴含更广!“型”的本义乃铸器之法,木制曰模,竹制曰范,泥制曰型。瓣型学说的“型”,不仅仅只是“造型”、“类型”,更是一种规范!同时还包含了形、色、品、格、神、韵等诸多与“型”相关联的要素。瓣型之“型”,基本可以说凡与国兰相关的几乎无所不包... ▲春兰传统品种“西神梅”... 从那些流传下来的众多古谱典籍及目下所见,均可以印证瓣型学说的此种全方位。比如说,就外相而言,老谱所载不仅只是论瓣(含外瓣、捧瓣、唇瓣),还论根、论叶、论甲、论芽、论苞、论蕊、论壳、论筋、论梗、论簪、论苔、论点、论鼻、论色、论香、论肩、论守,等等等等;就品种而言,不仅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瓣型花、素心花,还有红素类的“朱砂兰”,蝶花类的“蝶兰”,奇花类的“情兰”、“双兰”(双舌)、“品字”(三舌)“四喜”(四舌)等,色花类的“朱兰”、“雪兰”、“金兰”“紫兰”、“墨兰”,型色双艺的“金水仙”、“金荷”、“红梅”,等等;近代及当代,菊瓣、牡丹瓣、麒麟瓣(狮子头)、树形花、波瓣、飘门、百合瓣、水晶、麟生体、叶蝶、叶艺等众多新类型的发现及相关词汇的诞生,均得到了广大兰友的基本认同...由此可见,曾经、当下乃至今后,“瓣型学说”,都是开放的、演进的、发展的、更迭的、扩容的、与时俱进的、不断自我完善的。我们的名族文化特色之一,是自发形成,先流传于口头,后归结为文字,顺天应势、博采众长,宽进严出、优胜劣汰,集思广益、精华永存。如前所述,瓣型学说正是这样的产物... 自宋《金漳兰谱》所罗列的一众品种,紫兰、白兰的归类,下品、中品、上品、品外之奇等的排位,即可视作“瓣型学说”之源起;瓣型学说的起飞,是源于江浙春蕙兰资源被逐步开发后,一些过去主要以墨兰建兰为主体的资源中没有出现或较少出现的一些新优类别渐次进入了兰人们的视野,这些类别是符合其时国人的主体审美眼光及审美潮流的。瓣型学说籍此得以渐次丰满,并藉由鲍薇省等的记录得以明晰。同时,一些明显具有建兰种类特征,符合主体审美标准的东西还是被保留沿袭了下来,比如素为上、灯芯梗、主瓣盖帽、外瓣拱抱等... ▲中国兰花瓣型架构示意图...纵观瓣型学说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一个开源的,在传承沿袭的基础上,不断自我进化、自我更新、汇集众智的开放体系。随着寒兰、紫秀、豆瓣、送春、秋芝、红香妃等兰种及秦岭、大西南等新兴资源产地的陆续加入,为适应一些新出现的新优品类,瓣型学说的再次扩容无疑是必然的... 以变应变,以恒变为不变,是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同时也是瓣型学说的常态。变的是皮囊,不变的是筋骨,是中华民族对“真、善、美”恒久不懈的追求与探寻... (全文完) 点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huaf.com/lhjz/8704.html
- 上一篇文章: ldquo兰韵翁源rdquo过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