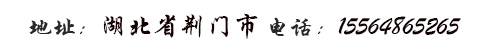猴子
|
北京治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so_4782785.html 如果人是聪明些的无毛猴子,他如今彻底的无神主义便不足为奇了。十二岁时,当颅中的浆糊还未聚作大脑,王星远已习得了敬畏。他正频繁地去往被称为学校的圣殿,朝拜被称为教师的诸神,再恭听被称为家长的牧师的教诲。十三年后,冥王星的照片传回了地球,何田田为冥王星PS上笑靥,配文:我们没有忘记你。 我兴奋地走进教室,一眼望见末排中央的四个高大黝黑的女生,又扫视一圈教室,后悔自己来到这个见鬼的地方。择校考试在四个月前,那天我见到许多漂亮的女孩,在排队去食堂时我暗恨与我牵手的女生竟非最可爱的那位。 我来到沉金中学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绰号为烤乳猪的小学班主任向我家长推荐这个学校,说这里治学严格。第二是我是择校考试的第一名,家长图个吉利,希望我也能以第一毕业。第三是择校考试的所见让我觉得这里的女生最美丽,我想和美丽的女生们做同学。当然,第一个原因是决定性的,因为烤乳猪和家长的共识是我需要收收骨头。 但由于第一第二个理由和我没啥关系,第三个理由的颠覆本应是灾难性的,因为接下来的四年班里很可能不会有美丽的女同学。但十二岁时,我的颅中同是浆糊,没有意识到此事的严重后果,我很快便被教英文的新班主任的裙子吸引了。 全球性感女神top的榜单在贴吧上已经流行,美不美先看腿一类的互联网箴言也屡见不鲜。但我对性的了解也只局限于杂志尾页的午夜热线的配图,感官也暂是有官而无感,那些top的脸和腿便还没变作女神。我只看到那条红色的裙子,上面有黑色的雁影和黄色的小花,停驻在夕阳融作的暮色里,给我一种奇异之感。王星远之后提过一个词叫萧凄,我就立刻想起了那条裙子。 裙子的主人,据我妈说,是个研究生毕业没多久的姑娘。她先是知道我喜欢踢足球,便要我做体育委员。她又发现我做操实在僵丑,便让王星远替了我的职。我会在考试后求她先批我的卷子,她打满分的时候我冲着她笑。她会在下节课向我提些巧妙的问题,我答不出的时候她冲着我笑,睫毛扑棱扑棱地闪。她的口语很好,能在美音和英音间切换自如,我们常希望播报下次听力考试的是她而不是教导主任。她教授L,R,和TH的发音时总是仔细,在那堂公开课后更是不厌其烦。 公开课上,她问:Whatdoyouguyswanttobeinthefuture?宗扬答:Iwanttobeascientist,因为我喜欢读十万个为什么。孙福答:Iwanttobeasoldier,因为我想保卫我的祖国。何田田答:Iwanttobeanastronaut,因为星星非常美丽。她问王星远:David,whataboutyou?王星远答一愣,答:I’llbeakillerinthefuture.我坐在最后,听课老师们的头都转向王星远,整齐的动作扬起一阵风,我觉得我的刘海被吹向右边。她也一愣,又问:MayIaskwhy?王星远答:Because…嗯…becauseofmoney,and…becausekillingisgood,sometimes…Ithink.王星远L,R,TH的发音都和她教的一模一样,钱和杀人则与所有老师教的毫无干系。在她又一次愣神的时候,听课老师们的头转向她,教导主任的头转幅尤大转速尤快,他的残发都因生成的幻影而变得茁壮茂盛;又扬起一阵风,我的刘海应该回到了原位。她似乎有些想笑,又似乎被教导主任茂盛的残发制止,只是敛容说:Ok.Pleasesitdown.Nowlet’sreadthesecondparagraphtogether. 第二天午休的时候,我被生命科学老师叫到教室办公室,他让我下节课不要再对着女性生理模型“唧唧咯咯地贱笑”,我争辩我是被唧唧咯咯地贱笑的卜秋弈传染的,他才是罪魁祸首。生命科学老师说卜秋弈唧唧咯咯地贱笑是他不对,但我唧唧咯咯地贱笑也不对,他又说全班所有人唧唧咯咯地贱笑会让他也想笑,那样课就没法上了,生理模型就没有用了,他最后说如果实在想笑就在心里笑。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挺在理,未及承认,听到有人敲办公室门。 敲门的是个时髦的女人,衣服毛茸茸的,首饰金灿灿的,让我莫名地联想起屠户和鹦鹉。但她并不聒噪,走到班主任桌前,轻声说:小周老师,我来了,抱歉那么麻烦您。班主任站起来说:您不客气,还麻烦您特地跑一趟,您跟我来。女人说:实在是抱歉,王星远他爸爸一会儿也要过来,我电话里劝不住他,您知道的。班主任说好的没关系,又问生命科学老师我们聊完了没有,叫我去找王星远,把他叫到教导处。王星远的妈妈和班主任走出了办公室。 学校不大,王星远的去处更少。虽然运球和投篮有些蠢笨,但王星远跑得很快,跳得还高,更能轻盈地滞空,我们就叫他猴子。我去篮球场找他,他没在。他能找到莫名其妙的书,前些日子捧着本爱情中毒症,最近好像在看美国风情录,课桌里总有一本脏兮兮的基督山伯爵。我去教室找他,他也没在。学校的伙食很坏,他的胃口却很好,很多同学刚扒拉两口时他往往已吃尽了,然后打一个怪味的嗝。这让他常去厕所,他总喜欢拉我一起去,我不愿时他会用一块钱引诱我。我去厕所找他,果然在那儿。他没手纸,我回教室取了何田田的三层餐巾纸递给他,然后和他一起去往教导处。 班主任和王星远妈妈已在那儿。教导处主任是个小老头儿,人小头小,脸上沟壑纵横,像是烤过头的泥盘。坐在他对面的是个矮个红脸的胖子,面沉似水,五官挤兑在一起,像个巨型柿饼。胖子看到王星远进来,眼皮一翻:小赤佬又帮我惹祸!对得起那么多老师吗?言毕就想动手,被教导主任拉住,转而向女人道:侬这戆女人教出来什么丢人现眼的东西?侬讲侬天天在外面鬼混点啥?放学了叫他来我家!你不教我来教!女人冷笑,叫他少说两句。班主任也劝他消消气,打发我先回教室自习。临走时我撇一眼王星远,他毫无表情地回望。出门后我仍听到胖子的吼声。 放学路上我问王星远怎么他爸爸那么凶,王星远说他就是那样。我问王星远今天是不是要去他爸爸那住,王星远说仍回自己家。我又问王星远他妈妈也要打他吗,王星远说不打也不怎么管他。王星远问我我爸妈怎样,我说还行,倒不会打我。王星远问我想不想吃盐酥鸡,我说我没钱,他说他请客,我说吃,他掏出十块钱,还额外买了两杯奶茶。我们坐在学校小区里的跷跷板上,他的腿在空中晃荡,边吃边说他在教导处的见闻,说好像这次公开课有区里的领导, 好像教导主任批评了班主任,好像要整治什么松垮的风气。见我听得兴味索然,王星远说他之后想试试抽烟,他好奇为什么人们知道香烟有害健康,却仍照抽不误。 周五的班会课开始时,王星远当众宣读他事先写好的检讨书,之后班主任毫无评述,宣布进行每周一次的班委会选举。选票是不记名的,竞选大队长时居然有人给王星远投票,王星远名字下便有个”一“字。周一的年级大会上,教导主任照例表彰了最近成绩突出的学生,又言及最近部分学生和班级的自由散漫,再大谈文化经典精神风气思想道德未来目标,同学们照例鼓掌。会议过半,便是”文化交流“的环节,学校请了位市特级教师,据称是个意识流大文豪。文豪分发毕他一篇关于女警察还魂的短篇大作,开始讲解,三句话中便有一句提及意识流三字,什么”意识流好啊”,“这就是意识流,懂哇”,”你们感觉到意识流了吗?“的评述互动更是循环往复,同学们从未听过如此声势浩大羚羊挂角的讲座,皆尽瞪圆双眼以求究竟。讲座将毕,文豪话锋一转,盛誉女警察之魂灵的高尚情操与中正美德,并期劝读者们以为楷模,同学们恍然大悟,照例鼓掌。 预备班的一年很快结束,班主任不再教书,跑到瑞士生孩子去了,我便没有机会再见那条红色的裙子和融化的夕阳。王星远已经学会抽烟,据他说还抽过雪茄,偷拿客户送给他爸爸的。那本基督山伯爵已经不见,替而代之的是本叫什么查克拉斯如是说的书,上面歪歪扭扭记着很多他的笔记。我翻看过一次,依稀记得在说什么骆驼狮子婴孩,还提及了桥和超人,和其他书不太一样。我也已经发现班中女生并非绝不可爱,比如当时末排的四位女孩中那个叫何田田的就很好。她的皮肤比雪还白,腿比旗杆还直,说起话来声软音糯,数学总是数一数二,敬礼和做操的时候则草草了事,像犯了软骨病。我奇怪为什么当时觉得她皮肤太黑,可能是因为校服太绿。 一位仇姓政治老师成了我们新的班主任,一米八的女人,也可能一米九,反正比所有同学都高很多。第一节课上,她说因为她向政府投诉取钱不方便,于是学校对面便新开了一家工商银行,然后她说我们应该感谢她,她说她代表了群众,是群众的力量让银行开门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政治课中听到一个玄秘的政治概念被事实阐明。除政治活力外,精巧的判断也是她智慧的表征。由于多动症是青少年中众所周知的最常见的疾病,也碍于反社会人格这个概念尚未流传,仇老师的洞见是王星远铅中毒了,医院查查指标。她又奉劝大家以后不要吃铅笔芯,并引她过去因铅中毒而中考落榜的学生为诫。她自滔滔不绝时,出于对她身高的好奇,卜秋弈借口上厕所路过讲台时站在她背后略有停顿,回来后问我们对比的效果,我们答:高,是真的高。仇老师好像察觉到什么,问王星远以后还吃不吃铅笔芯了,王新远说他从来不吃铅笔芯。仇老师有些生气,说橡皮屑也不要吃。 有几个班级里的男生爱和我玩。我喜欢放学打篮球,大家也喜欢放学打篮球;我喜欢看龙珠漫画,大家也喜欢看龙珠漫画;我喜欢上课吃早点,大家也喜欢上课吃早点。仇老师断定我是班级风气不正的根源,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为老鼠屎。老鼠屎被调到最后一排的单屎座,但老鼠屎没有流下鳄鱼的眼泪,因为何田田坐在老鼠屎的前面。何田田并不避讳老鼠屎,她会在上课的时候和老鼠屎在课桌下传纸条。传纸条的时候老鼠屎碰一下她的腰,她把手伸过来,有时手指会相互轻触。老鼠屎有一个mp3,何田田也有一个,老鼠屎给她放老鼠屎喜欢的挪威的森林,她说她家有本同名的书;她给老鼠屎放myheartwillgoon,回家后老鼠屎第一次因电影而落泪。老鼠屎在纸条上写:ifIjump,willyoujump?纸条传回来,上面写:Iwilljumptoo.老鼠屎在小区的一颗树下挖了个老鼠洞,将纸条藏进洞中,希望它能永垂不朽。 做粥的厨师应是个神经大条的家伙,他不仅允许老鼠屎在锅中胡搅蛮缠,更将一些米粒遗落于锅外。王星远变得越来越离群,总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连球也不怎么打了,体育课自由活动时便茕茕独行在两百米的跑道上。我在篮球场招呼他:喂!猴子!过来打球!他只是冲我摆摆手,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像是个猴子,倒像是个蜗牛。午饭仍是吃得精光,打出那怪味的嗝后,便会开始读他的查克拉斯如是说。查克拉斯如是说并不是本厚重的书,查克拉斯应是没说怎么让自己不被没收。 那天,可能因为政治活动不太顺利,仇老师心情不好,她走进教室,目击我和卜秋弈纸未及藏起的纸制碰碰车,过来把碰碰车撕成四片,再揉成纸球,骂我又一次坏了一锅粥,骂卜秋弈不学好并因此道德直线下坠,说我和他真是难兄难弟。她挥斥方遒之际,瞥见王星远正若无其事地看查克拉斯。学童的漠然刺痛神经,师长的尊严燃作怒火,仇老师的身高忽更暴涨数寸。她流星般飞冲至王星远身边,从他手中夺去查克拉斯。仇老师似乎想把查克拉斯同样地一撕为四再揉成纸球,但查克拉斯骨头很硬,在两次失败的尝试后她只得用拇食两指紧捏查克拉斯的封面,以将被倒提着的查克拉斯在王星远面前抖动,查克拉斯发出飒飒之声。她怒喝:你来学校就是来看闲书的?王星远沉默。她怒喝:你成绩那么差还天天看这种东西?你要不要脸?王星远沉默。她怒喝:你不说话?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王星远沉默。她怒喝: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管不了你了吗?叫你妈妈明天来学校!王星远不复沉默,说:好。她又尝试撕开查克拉斯,但又失败了,转而叫班级同学放学都别走,带着查克拉斯出了教室,并自言自语:猪狗不如的东西。教室很安静,午休结束的铃声有些孤零零的。 我不知道王星远的妈妈后来是否来了学校,但我知道王星远的爸爸后来死了。有块黑布在王星远绿色校服的手臂处挂了一个月,显得突兀与不详。我觉得如果我的爸爸死了我会难过。于是,有几天我没买故事会,攒下七块五,请王星远吃盐酥鸡,并额外买了两根香肠。我们坐在跷跷板上,王星远问我和何田田怎么样,有没有接过吻。我说没有,连手也没牵过,问他怎么问起这个。他说他最近在谈恋爱,和一个网名叫影月的女高中生,又说他们怎样一起划船和在桥洞下接吻。王星远说影月和自己很像,我问像在哪里,他想了一会儿,说影月左眼角有一颗黑色的泪痣。夜幕降临,王星远点燃了一支烟,借着火光我望他,他左眼没有泪痣,右眼也没有。他说他很喜欢影月,却不想更接近她。我觉得奇怪,问是不是因为她太老了。王星远笑,说不是,又问我知不知道阴郁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差不多知道,王星远说她太阴郁了,我哈哈地笑,说他自己也没怎么开朗。王星远也哈哈地笑,说这就是问题。我提起他爸爸的死,问他是不是还好。他说还好,有时候也会想起他爸爸,他没想到他的妈妈居然非常伤心。 今明被昨日之引力拉扯作相似的形状,分子的上限乃由阿伏伽德罗钦定。四年过去了,我仍未与何田田牵手,但我们周末的时候会一起在校外补课,那让我感到快乐。在王星远快乐的日子里,他会逃学跑去公园,坐在长凳上看鸟,看公园棋手们对弈,看老太太老先生们打太极拳,然后读他的闲书。王星远告诉我他甚至学会了放风筝,那让我有些羡慕。无聊时我会望向教室窗外的天,试图找寻他的风筝。风筝是寻不见的,有时能看到鸽子飞过,我便想象风筝和鸽子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引绳隐没在蓝天白云里,另一端是王星远轻快的笑脸,也许影月就在他的身边,也许她也在笑,也许她泪痣的眼睛是弯弯亮亮的。 我和王星远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中考结束那天,我们去网吧打游戏,结束时已是晚上,我意犹未尽地说过几天再一起去网吧。王星远说他暑假要和他妈妈一起回老家,暑假结束的时候回来,到时候再一起玩。我说好。临别,王星远说他再抽支烟。黄梅雨还没停,淅淅沥沥地打在地上树上,我们躲在杂货店的屋檐下,有位客人买了包餐巾纸,彼时路过的垃圾车放着。我在心中默想歌词,方至满庭花簇簇一句,垃圾车开远了,我也便想不起下一句了。王星远撑开他的伞。“晚上有点凉,走了”,他说。“是有点凉“,我说,“再见啦“。我们挥手,转身,各自朝家的方向走去。 整个暑假,王星远的qq头像都是灰的。中考成绩出来,我不是年级第一毕业的,索性还也不是最后一名。暑假结束,王星远的qq头像仍是灰的。年轻人是向前看的,进了高中,我也渐渐不常想起初中,虽然我与何田田见面时会偶尔聊起那时的事。何田田说她有一次在初中的小区里又一次碰见了仇老师,仇老师说若非她辛勤的政治运作何田田是不可能被保送到市重点的,她相信何田田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并强调何田田的父母无需特别地感谢她。为了突显她的能力与功绩,她最后指出王星远之流之所以落榜是因为被她放弃了。我问何田田仇老师有没有提王星远在什么学校,何田田说仇老师说话的时候口水都喷在她脸上,她只想逃回家,就没多问。我想起仇老师眉飞色舞的样子,觉得有些可惜,因为没能知道王星远在哪儿。我们奇怪为什么王星远就这么消失了,何田田说是不是因为中考没考好有些不好意思,我说王星远不会如此在意中考。 但王星远确实是消失了。一晃很多年,冥王星的笑脸教我想起了他,虽然我已记不分明他的笑脸。也许未来的哪天我们能履行未践的约定,再一起去次网吧玩下游戏,再吃份盐酥鸡喝杯奶茶,或者他向我展示他的风筝,我再问问他与影月的恋情。我觉得如果我提起影月,王星远一定会笑,就像我若提起初中老师,唐太斯,或者查克拉斯那样。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huaf.com/lhpz/4755.html
- 上一篇文章: 空谷幽兰兰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