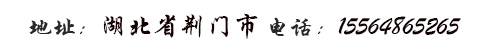铃兰四月,不能只有花开
|
四月,不能只有花开 文图/铃兰
离清明还有两天,母亲领着我们姊妹5个去给外婆、外公上坟。天气晴好,伴有微风,天气预报说清明那天会下雨。有雨就对了,清明就该是雨纷纷的日子。
今年春暖,老家的桃花、梨花已开。自从前些年村民开始种果树,村外那些原本种小麦和玉米的土地就换成了果树,每逢春暖花开,那粉的、白的花儿,像是给土地穿上的漂亮花衣。人走在园子里,就有蜜蜂在身边上下飞舞,人忽然就成了开着的花儿。外婆、外公的坟就在那开满粉色、白色花的南坡上。
古人智慧,把祭祀先祖和祭奠亲人的时间定在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似乎也寄托着生命重生的美好愿望。坟地上的小草已冒出了嫩芽,新绿盎然却不能激起内心的一丝欢喜。脚踩在枯草旧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这响声是多么熟悉呀!那难忘的年少时光。
北方的冬季冷,充满智慧的先人们就在屋里盘土炕取暖,但烧炕就需要柴火。童年时,我家和外婆家的村子还没有开始种果树,庄稼少得可怜,柴火刚够平日做饭用,烧炕用的柴火是村外树林里的枯叶。背回来的枯叶和麦糠搅在一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柴火过冬。所以每年秋季树叶开始落时,外婆就开始一点点地积攒落叶,待到深秋,落叶厚积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便会去帮外婆搂更多的树叶。如今想来,那时之所以满心欢喜地去做某件事,好像不全是出于爱劳动,而是那项劳作中必有着平日里少有的乐趣。
在村外的树林里,我们抱着可以摇动的小树挨个晃,唰啦啦……唰啦啦……飞落的叶子像仙女洒下的花瓣,滑过肩头、胸前。我站在树下,将头仰得高高的,张开双臂转几圈,感觉自己就像个公主。蓝蓝的天空有小鸟在飞,也幻想自己就是自由的鸟儿。
树林里有槐树、桐树、椿树,桐叶大而蓬松,槐树和椿树叶细小密实,我们都喜欢搂桐叶,几筢子下来就是大大一堆,显得很有成绩。外婆说,可别看碎小的槐树叶,它和麦糠混在一起才是煨炕最好的柴火。外婆还说,桐树叶看着大,不经烧,就像有人长得好看啥也不会干,有人长得不算好看但勤快能干。几个小脑袋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我们玩得差不多了,就赶紧把搂好的落叶装进背篓,外婆说压瓷实,可以多装点,能少跑几趟。
竹编的背篓口大底小,像采茶女背的那种小背篓。那时我八九岁,背篓立起来比我高。装满树叶的背篓又高又沉,外婆瘦小,还有一双小脚,所以背着背篓走路很吃力。我们会抬着背篓底跟着她一起走,以减轻外婆肩部负重。外婆不要我们抬,说娃小不能用劲太多,会长不高的,我们信以为真。长大后才明白,年少时幼稚只觉得搂树叶有趣,哪里能体会到当时外婆家的清贫和外婆对我们的疼爱呢。
外婆背着竹篓往回走,我看不见她的头,只看见背篓和背篓下那双三寸金莲在向前移动着,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长大几岁后,那画面总会让我的视觉和思维错位,认为那就是个长着一双小脚的大背篓,行走在深秋。
不管时光走得有多远,我依然怀念那片树林,怀念林间的沙沙声响,因为它所赋予我们的不仅是土炕的温暖,更让贫瘠的心灵有了臆想的空间。
外婆、外公的坟前已摆有水果点心,应是舅舅或者表妹来过。坟前的那棵柏树长高了些。柏树是三舅几年前栽的,三舅细心,在树下修了小渠积雨水,但柏树不好活,两棵只活了一棵。
大弟在坟头上压了黄纸,然后跪在墓碑前点燃了纸钱。南坡上风很大,母亲每放一沓纸钱就会被风吹走几张,二弟用树枝挑拨着没有烧尽的纸钱,我们姊妹三个跪在母亲身后。母亲像往年一样,边烧着纸钱边对外公、外婆说着话,可没说几句就哭了。母亲的哭声里传递的是女儿对父母的思念。我能感受到,因为我的眼眶也是湿润的,心里也思念我的外婆。外婆离世的十多年里,很多个清明节和寒衣节时,她总会来到我的梦里,不言也不语。那佝偻的身影、慈祥的面孔,与我若即若离,而我每每都是在欲喊无声地急切中惊醒。
我多么希望,在梦里再听到外婆说我是个有福之人;我更想再听外婆讲她的坎坷故事。最好还是儿时的夏日,外婆摇着蒲扇,我靠在她的腿上,双手摸着她柔软细腻的胳膊,感觉好舒服。外婆本是小家碧玉,战乱时,从河南渡过黄河逃到陕西。
那年外婆十四五岁,日本人侵略到她的家乡,男人们组织起来保护女人和孩子出逃,外婆的母亲给她和她的嫂子备了盘缠和干粮,让她们渡过黄河去逃命。脸上抹着锅黑的外婆哭着告别了她的母亲,她和嫂子抱着正在吃奶的小侄子,跟着乡亲们离开了村庄。他们前脚刚走,日本人就杀进了村子,听见枪声和哭喊声,他们不敢继续走,就躲起来等天黑再走。在惊恐的躲藏中,外婆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和乡亲被赶到村外的麦场上。一阵机枪的扫射后,她的亲人们都躺在血泊里。外婆说她当时被吓得浑身发抖,已不会哭了,嫂子怕小侄子哭出声来,边流着泪边将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
为了逃命,外婆只带了她母亲留给她的一对银镯子,是多股银丝拧成的麻花状的那种镯子,将其余的细软埋在了一堵墙根下,并做了记号,心想着等回来再挖出来。那时候年龄小又单纯的外婆哪里会想到,与家乡一别竟是一生。(后来有条件回乡探望,但因为外婆当时年龄小没记住具体地址而无法找寻)后来和外公成家后,为了一家的生活,外婆将唯一的嫁妆——那对银镯子,也变卖补贴了家用。至今母亲说起来还感到惋惜。
外婆和嫂子随着逃难人流到了陕西咸阳城,她们栖身在城北的破窑洞,那里是难民的聚集地。后来,纺纱厂来破窑洞招工,为了生存,外婆谎报年龄才进了厂子。虽然纱厂干活累,吃住也不好,但总比在破窑洞风餐露宿好。几个月后,等她回到窑洞,发现嫂子和小侄子都不见了,此后再没联系上。外婆说她的嫂子多半是带着小侄子嫁人了。于是,在他乡异地的外婆成了个孤女。
进纱厂后没几年就有人给外婆介绍了外公。外公祖籍山东,也是父辈逃难来到陕西。外公兄弟三个,家住在咸阳城北北蟒山下的一个村子。外公个高,脾气直,有着山东人的特点。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一个外地人,尤其是外地女子,要在城市里生存是不易的,若在乡下好歹有土地饿不死人。于是外婆决定离开城市,离开纱厂,为了活下去就嫁给了大她好几岁的外公。后来就有了大舅、母亲和三个舅舅。外婆说她跟了外公后没少挨打挨骂。打我记事,外婆总是温和慈善的样子,外公虽然脾气直但秉性善良。我始终无法想象外公和外婆在缺吃少穿的年代,是如何将几个孩子拉扯大的。这些母亲是知道的,但我不愿意再提及那些往事使她伤心。
一股风吹过,纸灰随风飘向远处。母亲说,外婆从没去过她的梦里,也许是怕她难过。每次提起外婆,母亲都会说这话。外婆是爱母亲的,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又怎会不思念。也许外婆一直就在母亲的梦里,只是母亲不曾记得。
我知道,陪母亲一起给外婆上坟的机会会随着母亲白发的增多而越来越少。总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像母亲这样哭在我的母亲坟前,而我的儿女也会跪拜在我的身后,哀伤地想念他们的外婆。虽然明白人生就是这样一代代地延续,谁也躲不过逃不掉生离死别,但是,当那些不敢触及的画面在我脑间晃过时,心就会绞痛,让我时常感到惧怕。它们似乎很遥远,远得像外婆离开我们已快20年了;却又似近在咫尺,近得好像昨天外婆还在教我做馍馍。
人这一生会经历很多,需要铭记的人和事也很多。外婆说人活着要实实在在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我听了外婆的话,铭记这一生需要感恩的不仅是赐予我生命的父母和我血脉相连的至亲,还有珍惜我和我珍惜的朋友。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来南坡,总见添新坟,那些黄土堆上或长草萋萋,或柳枝斜插,而每个土堆下,都埋葬着曾经鲜活的躯体。那一堆堆黄土,堆砌的也是隔世的思念。四月里,不管周边那些粉、白花儿开得多鲜艳,不管雨天晴天,这冷冰冰的黄土堆,总使那些花的艳带着哀愁。
人,其实就是世间的一粒尘,不论飞得高低,不论活得长短,终究都得归于尘土中。表弟小鹏那年刚结婚,二舅家喜添新人,不曾想,1个月后又办了丧事,表弟出车祸走了。遗传了外公身高基因的二舅像被抽了筋瘫倒在床;嫁到陕西二十多年还带着川音的二舅妈更是心痛成疾,瘦得没了人样,几年缓不过劲来。如今,表弟在这已经伴着外婆、外公快10年了,他就躺在二老脚下。每年祭拜完外婆、外公,我定要给表弟烧些纸钱,他的模样我还记得清楚。
后天就是清明节,但愿预报的那场雨能来,清明就该雨纷纷。
作者简介:铃兰,本名张艾,陕西咸阳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爱文学、摄影、远足,好诗词、散文写作。追求恬淡、优美、空灵之文气。有作品发表杂志报刊,著有散文集《艾语》。 家长对比了,都说实惠! 彩版精装,页,售价元包邮 (知名图书网站售价元) 购买请加我平台编辑
↓点击阅读往期精彩↓ 小说 西北作家 周末版 杨争光小说专辑 西北作家·周末版 秋子红作品专辑 美文 西北作家·周末版 赵丰散文专辑 西北作家·周末版 黎荔作品专辑 指尖:农人 刘凤珍:夜风(外一篇) 铃兰:坐在春天里 且诗且歌 周养俊:春之歌(组诗) 朴果树:春之絮语(组诗) 理论·评论 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阎连科:我的小说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单纯 声明:网络图片权属不详,如不妥请联系我们删除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huaf.com/lhfb/9185.html